3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第77个成员,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今年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亲历了中国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的全部发展历程。
中国移动通信的崛起之路:从3G到5G的跨越
邬贺铨:在3G的时候,中国的标准必要专利只有百分之几,在4G的时候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在5G的时候标准必要专利,中国占了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的34%,美国还不到14%。所以中国在5G上边,我们说我们能够称得上是超越了、引领了。当然未来6G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了。

今年是6G标准制定的启动年,回望过去三十年,从最早的拨号上网ISDN一线通,到宽带ADSL光纤入户;再到3G、4G、5G的层层跨越,如今,通信技术步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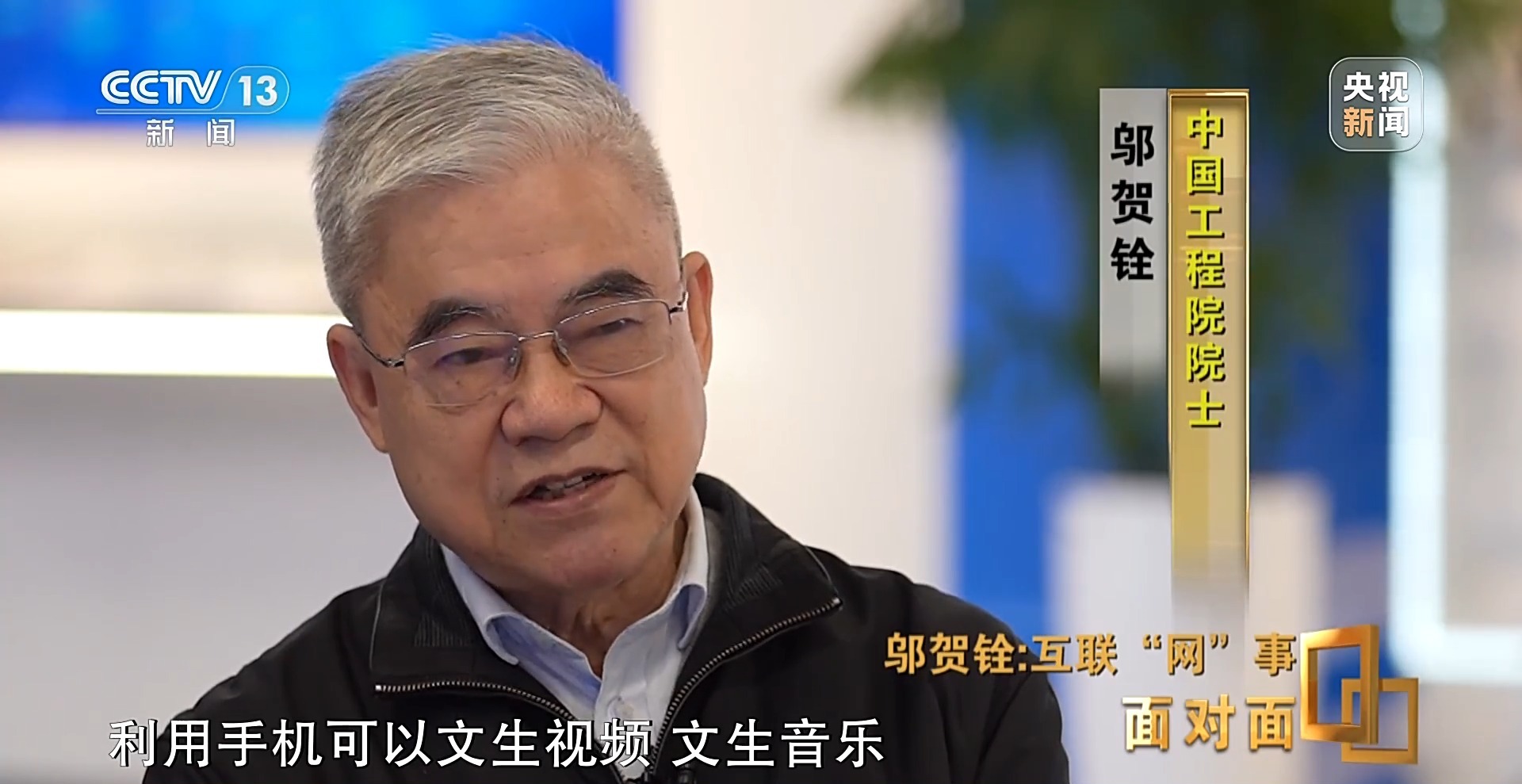
邬贺铨:未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精简可以落到手机上,并且再通过训练出智能体,相当于类似小程序,我们用户使用手机、利用手机可以文生视频文生音乐,还有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同声传译,还有可以跟残疾人对手语,甚至我们可以自动识别你在手机上通话的对方,究竟是真人还是假人,会不会有电信诈骗?这些能力手机上都会有了。未来终端类型更多了,除了手机、PC、眼镜、AR等等,所以会有一个AI终端的时代,我觉得会带动信息产业特别通信,移动通信产业新的飞跃。

6G新起点:技术竞争与未来挑战
6G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支持更高的传输速率、极低的延迟,将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6G技术纳入未来产业培育核心框架。然而,与5G研究相比,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封锁、 标准博弈、供应链安全等问题成为现实挑战,标准博弈也将因此更加激烈。在邬贺铨过往的经历中,中国提出3G标准时,就曾面对美欧两强主导的格局,但那也正是中国打破技术垄断的开始。
邬贺铨:在3G的时候,欧洲有一个标准叫WCDMA,美国有个标准叫CDMA2000,当然中国是TD-SCDMA,主要三个国际标准,中国有其一,但是欧洲从来就不用别人的标准,美国当然也不会采用中国的标准,他们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成功的。

邬贺铨: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打压呢?因为你的发展已经挑战了他们的霸主地位了,他们就需要用各种技术来延缓中国的发展,甚至阻挠你的发展,但是我感觉到中国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样子了,我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你越是抵制越让我不得不从零做起。
邬贺铨的通信科研生涯:从PCM到SDH的关键抉择
中国通信产业曾起步艰难,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通信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代通信科研人员之一,邬贺铨从模拟通信起步,亲历了整个通信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1969年,邬贺铨在四川眉山原邮电部505厂从事24路脉冲编码调制(PCM)终端设备的研制,这种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的设备,是数字通信技术的起步。基于美国提出的PCM24路标准,邬贺铨和团队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市话数字中继系统,但当时,欧洲提出了PCM30路的标准,中国数字通信标准面临着该走哪条路的选择。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该何去何从。时年32岁的邬贺铨在会上作报告,力主从美国标准转为欧洲标准,最终这次会议认可了邬贺铨的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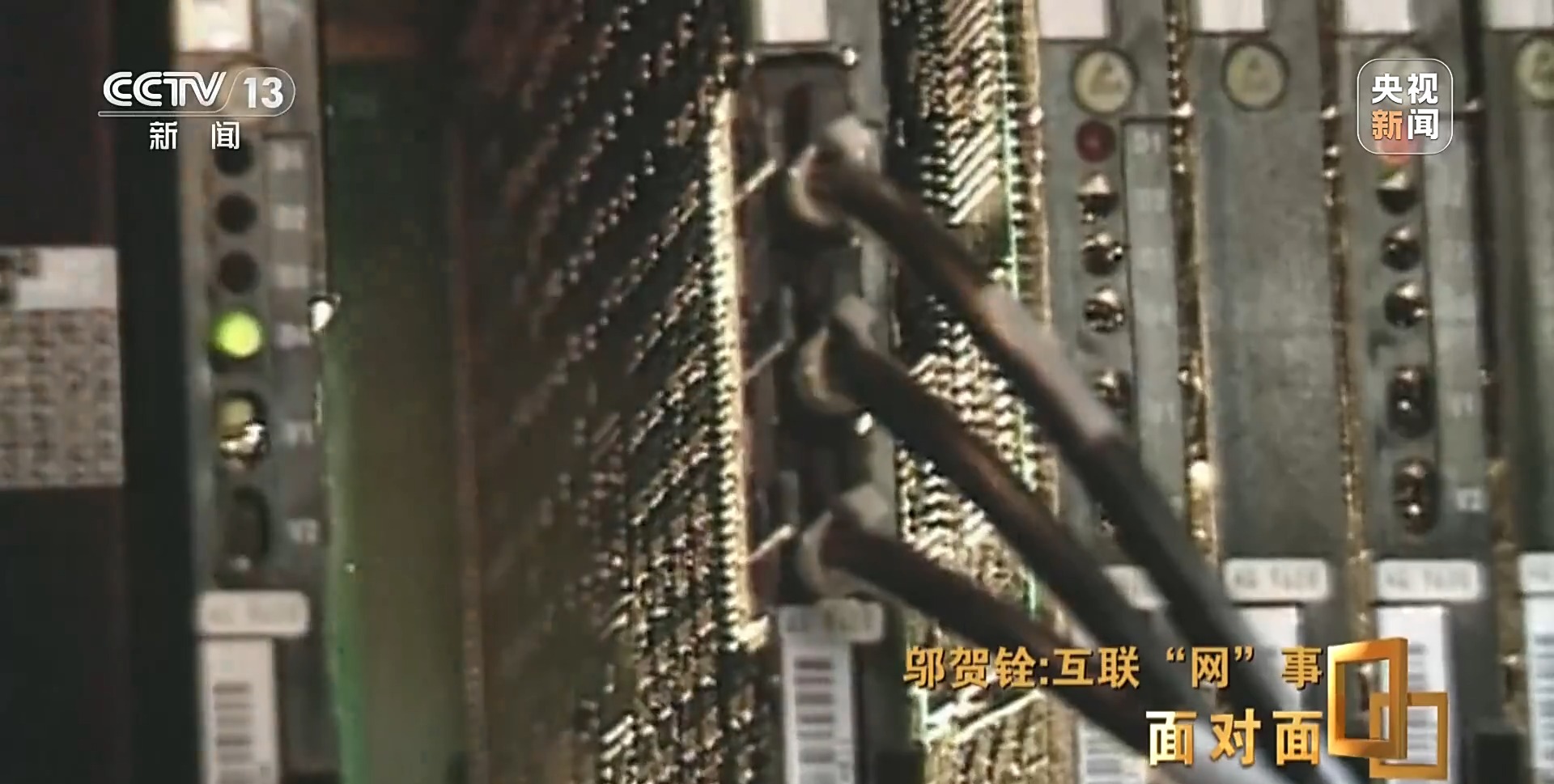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邬贺铨和团队承担了“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之一,565Mbps(兆比特每秒)五次群光通信系统的研发,使用的标准是PDH准同步数字体系。他注意到,国外在这一标准线下已经开始了六次群系统的研发,与此同时,国际电信联盟正在研究SDH同步数字体系,相比于PDH,SDH具有速率更高、灵活扩容等优势。

1988年,邬贺铨向邮电部提出建议:调整通信体制,从PDH过渡到SDH。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SDH的专用芯片,也没有测试仪表,要实现SDH的指针调整十分困难。在外界看来,这次转型无疑是一次冒险。

1996年,中国第一套国产SDH设备成功商用落地,缩短了与国外技术的代际差距,这一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通信技术水平,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同时也给出了重要提示:真正的风险不是转型失败,而是错过技术变革的时机。
TD-SCDMA:中国3G标准破局与产业链重构
自1993年起,邬贺铨连续“掌舵”多个国家重大通信研究项目,为国家通信产业发展谋篇布局,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崛起。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向全球征集3G国际标准技术方案,邬贺铨时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他坚决支持研究院提出的无线通信国际标准TD-SCDMA。然而,当时的中国通信产业,芯片、终端、天线、基站、软件无一不缺,他的想法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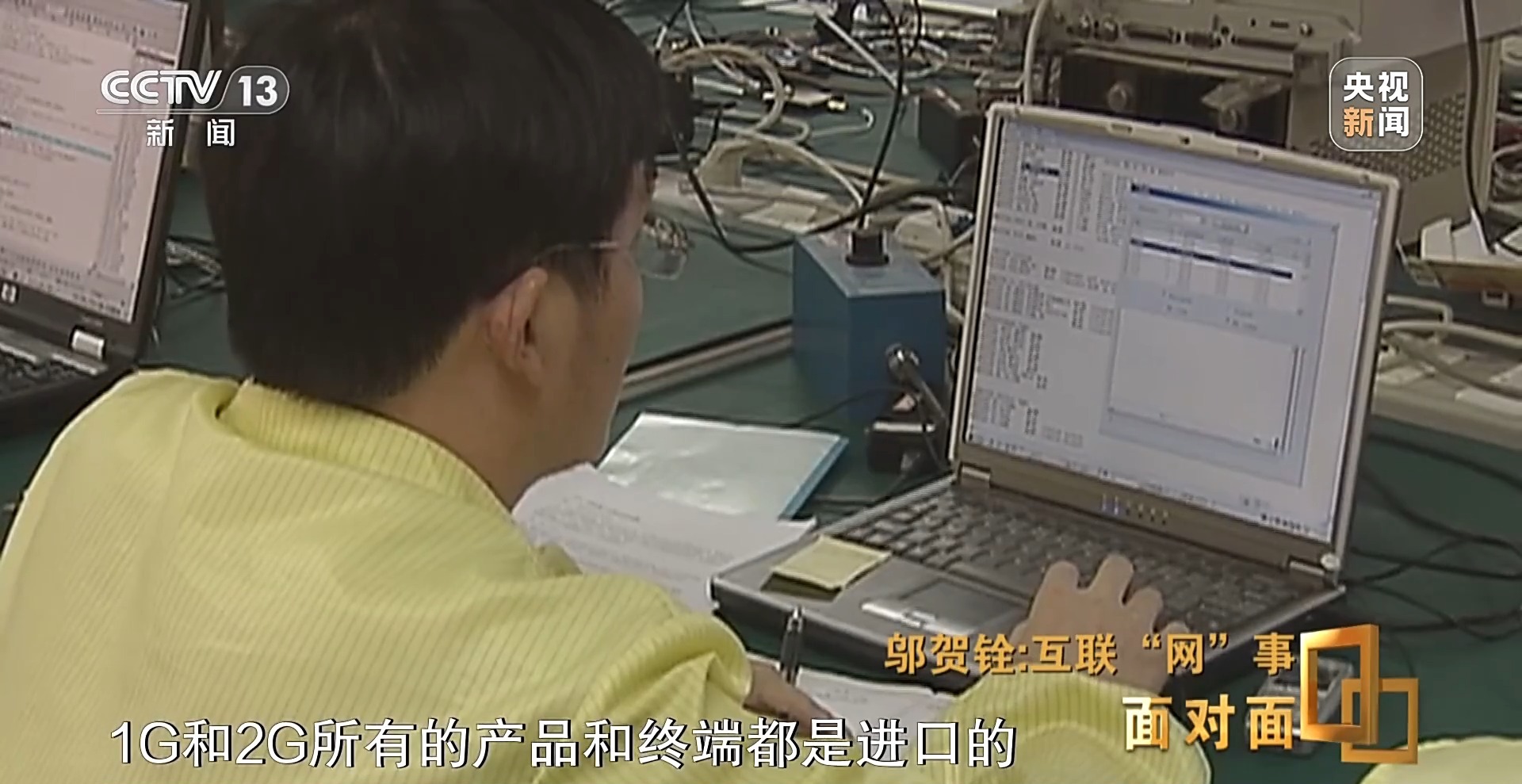
邬贺铨:1G和2G所有的产品和终端都是进口的,2G我们已经没有创新的机会了,人家标准早就定好了,什么都做了,产业也没我们的份,3G正好是换代,这是我们一个机遇,所以当时提这个标准。为什么中国能提出这个标准呢?第一中国是有技术基础,我们现在说创新需要胆大,但是我更认为艺高人胆大,没有技术是胆大不了的,传统的移动通信都是FDD频分双工,什么叫频分双工?来话占一个频段,去话占一个频段,来去相当于马路上一样有两个车道,一个是从东到西的,一个从西到东的,互不干扰,但是我们想在3G要往数据发展,数据来去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未来的视频你可能从网上下载多,你传回网上少,所以两边是不对称的,我要采用一种新的技术叫智能天线,不是一根天线,是多根天线,通过这样我可以提升我的效率,我们有了一定的创新技术,而且相信这个技术,适用于以数据为特征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当时觉得既然征集,为什么不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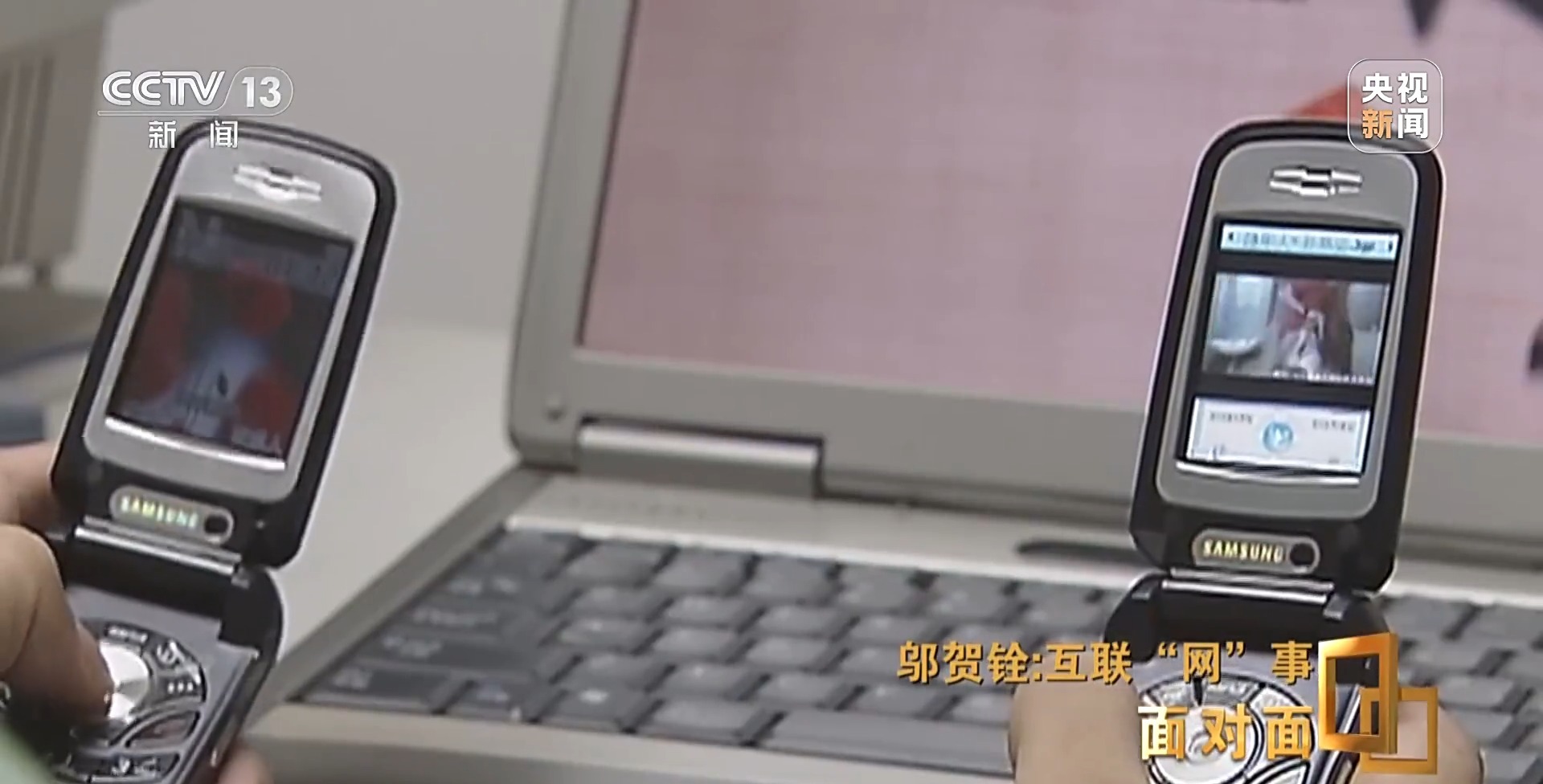
当TD-SCDMA成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时,中国通信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入局。
成为标准只是第一步,TD-SCDMA要走向市场,还需要大量的配套设备,而当时国内并不具备自主生产3G设备的能力,国外公司不看好TD-SCDMA,也不开发TD-SCDMA产品,想要将TD-SCDMA技术产业化,困难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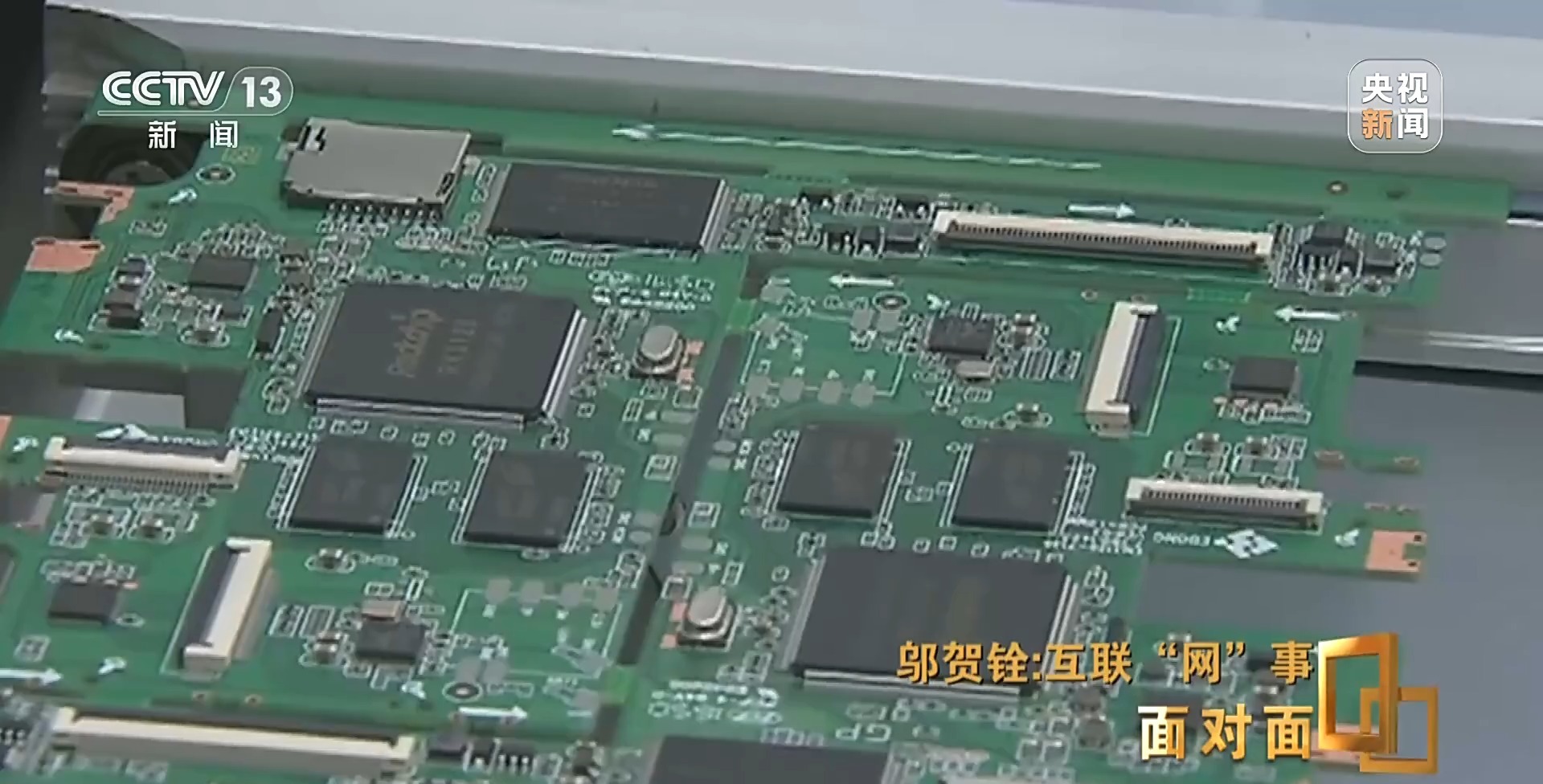
邬贺铨:我们不得不从零做起,我们说TD-SCDMA的成功不是说我们做出了产品,主要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创新链和产业链,现在反过来看,TD-SCDMA也有很多缺点不足,很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了从标准的酝酿到完善到研发到产品到产业链整个配套,到建网、部署、应用全过程,中国最早的通信产业我们没有光缆,我们是先从买光纤,自己造光缆,后来就到了我们自己造光纤,现在到了我们自己造光纤前端的预制棒,现在又到了我造生产光纤的装备,现在中国的光纤企业一年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光纤光缆。
记者:TD-SCDMA它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帮我们建立起了整个产业链。
邬贺铨:至少我们有信心,不单是科技人员有信心,政府也有信心,我们也是可以搞出一个自主创新的东西,将来比如说6G,哪怕你芯片等等有困难,我们也仍然能够做得到,我认为从通信技术的角度,这里边没有什么绝对跨越不了的鸿沟。

30多年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实现了从2G跟随、3G突破、4G同步,到5G超越的跨越。不久前,邬贺铨现身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和2025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82岁的他仍乐此不疲地钻研网络和通信技术发展前沿,力所能及地发挥余热。
邬贺铨:我现在还兼任了移动信息网络国家重大专项的总师,也就是谋划6G项目的这种组织,我们6G的网络不是简单的5G延伸,它需要在架构上有创新,现在的5G总体上是成功的,下行的带宽会比4G高八倍,上行高三到四倍,但是这种比4G速度的提升还没有能完全转化成消费者很好的体验,所以未来6G还得要下大力气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体验。
制片人丨刘斌 王惠东
记者丨董倩
策划丨陈朋
编导丨丁芳
摄像丨刘洪波 杨帆 高忠
责任编辑:丁超弋